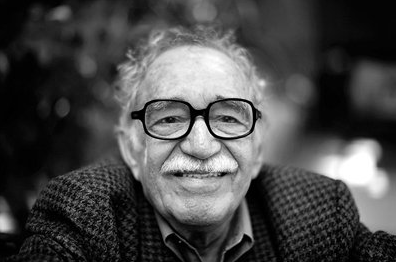人的性格是童年的回忆,童年是作家的“心灵故乡”和创作源泉。《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的童年是和外祖父母度过的,从出生一直到8岁之前,他一直和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外祖父母、姨妈、表姑奶和姑奶对其一生影响极大,其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常有其影子。
父母的长子
马尔克斯的父亲埃利西奥(1901—1984),1901年出生于哥伦比亚苏克雷地区的辛塞镇,他属于土生白人,也即他们的祖辈都是西班牙移民。埃利西奥是私生子,14岁才和亲生父亲相认。为了摆脱贫困和私生子的屈辱地位,他离开故乡辛塞镇,到哥伦比亚加勒比沿海城市卡塔赫纳市求学。不久即因缺乏经济来源而不得不辍学谋生。他先后流落科尔多瓦、苏克雷和玻利瓦尔等地,最后闯荡至阿拉卡塔卡镇。
从1904年到1910年,哥伦比亚马格达雷纳河流域大规模种植香蕉,使哥伦比亚的大西洋沿岸一带突然繁荣起来,形成了“香蕉热”,来自各地的人都云集在这个盛产香蕉的村镇。马尔克斯的父亲——埃利希奥就在该镇找到了一份电报报务员工作。尽管在学业上没有什么机会了,但他却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赢得了温馨的爱情。
192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埃利希奥结识了全镇最漂亮的姑娘——伊瓜兰,并爱上了她,姑娘对他也是情有所钟。他们的私恋遭到了女方父母的坚决反对。但是,姑娘对自己的情人坚贞不渝,并未婚先孕,姑娘的父母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并要求他们要远离阿拉卡塔卡镇。于是,1927年,两人移居里奥阿恰市。伊瓜兰即将分娩时,她的父母听到这一消息后,转怒为喜,老夫妇俩盼孙心切,便命女儿回到阿拉卡塔卡镇,以便使第一个外孙安全出世。1927年的3月6日,这个在日后的世界文坛上响当当的才子出世了,当时取名叫加夫列尔·何塞。
多鬼的房子
马尔克斯在8岁前跟着外祖父母居住在一座阴森恐怖的大房子(大屋)里。这座宅院的每个角落都死过人,都有难以忘怀的往事。每天下午六点钟之后,人就不能在宅院里随意走动了。那是一个恐怖而又神奇的世界,常常可以听到莫名其妙的喃喃私语声。
外公家由前院、房子和后院三大部分组成。房子颇具加勒比风格:宽敞、明亮、绿荫翳蔽的房间很多(据说有二十多间),它是《百年孤独》中布恩蒂亚家的主要蓝本。
据马尔克斯回忆,大屋的很多房间是空着的,其所以空着的原因是它们的居住者死了——可能是哪个亲戚,比如他的舅姥爷拉萨罗、姨奶佩特拉,或者姨妈玛尔加丽塔。为了纪念他们,房间一直空着。
住在那么一座大屋里,马尔克斯难免感到自己既渺小又胆怯,尤其是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房子变得静悄悄的……一到下午六点钟,大人就让小马尔克斯坐在一个摇篮里,对他说:“你别乱走动,你要是乱动,佩特拉姨妈和拉萨罗舅舅不定是谁就要从他们各自的房间里走到这儿来了。”所以,那时他总是乖乖地坐着……
马尔克斯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枯枝败叶》就描述了一个7岁的小男孩,他自始至终就一直坐在一张小椅子上。至今,人们依然觉得,那个小男孩就是小马尔克斯,在一座弥漫着恐怖气氛的宅院里,呆呆地坐在一张小椅子上。其生活环境造就了他童年时期静静地观察眼前一切的习惯。
多年以后,当马尔克斯不得不离开阿拉卡塔卡时,大屋就成了他最大的精神负担,因为他想用文学“成就它”,一半为了忘却,一半为了纪念。
迷信的外婆
外婆特兰吉利娜对于加西亚尔克斯,既是现实的,又是“艺术”的。他对她的记忆简直童话般地富有诗意。
当他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外婆就用上等的玫瑰花瓣给他治疗喉炎(据说是脐带绕脖所致)。后来,每当他打嗝或咳嗽,她就会用同样的方法给外孙治病。
母亲始终跟着父亲东跑西颠给他生下6个弟弟、4个妹妹,照料孩子的事就全交给了外婆。孩子的到来不但给大屋带来了生气,而且大大地缓和家庭气氛。孩子从未享受骑在父亲肩上逛街、趴在母亲膝下承欢的乐趣,但却很快成了外婆的宠儿。
儿时的马尔克斯总是醒得很早。每天雄鸡啼鸣、晨光熹微,外婆和姨妈起来烧早饭的时候,他也会果断地结束漫长的睡梦,回到外婆的身边。所有这些,都将进入他的记忆,成为拂不去撵不走的“幽灵”,从而最终进驻他的文学世界。比如,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第三次无可奈何》中,那个7岁的小孩在“死亡”中继续生长的噩梦,当与此不无关系。还有《枯枝败叶》中的那个11岁的男孩,他坐在摇椅上注视死人的目光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婆还是个相当健康活跃的女人,那时,她有五十多岁,她皮肤白皙、眼睛湛蓝,风韵犹存,她身材小巧,但性格坚毅。虽然头发已经灰白,但两耳皆聪,目光如炬。她始终穿着或黑或蓝的“丧服”或“半丧服”,一天到晚忙里忙外,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她总是边说边忙,自言自语,像《百年孤独》里的乌苏拉。
外婆是一位博通今古的人,她善于讲神话传说及鬼怪故事,对于马尔克斯的日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每天马尔克斯就坐在外祖母身边,听她漫不经心地一边干活一边讲的各种民间传说、寓言故事以及阿拉卡塔卡镇人民为描绘那个辉煌的“香蕉热”时代而编织的传闻。马尔克斯认真地听着,他被每一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所吸引。对于马尔克斯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外祖母往往都用一个长长的鬼故事来加以回答。和许多哥伦比亚人一样,外婆就是这样将历史、现实和迷信糅合在一起的。
因为好客,家里常常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他们有的是外公的战友,有的是其亲戚。除了朋友常来拜访外公外,外公还有很多私生子也常常到这里歇脚打尖——他和妻子是近亲结婚,担心无后,在硝烟弥漫的内战时期制造了至少9个私生子。不过,外婆却对这些私生子们没有反感,而且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地对待他们。
外祖母不仅慈祥地照顾着外孙,而且,她还是全家至高无上的女王,精明能干、精力充沛、子女成群、才识过人,她能身处逆境而不气馁,她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人口众多的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她既是家的统率者,又是带头人。因此,外祖母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频频出现,成为众多妇女角色的典型。
外公是上校
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尼古拉斯曾在“千日战争”(1899至1901年,哥伦比亚发生自由党反对保守党的内战,最后保守党获胜)中,在自由派将领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的指挥下,屡立战功,荣获上校军衔。
马尔克斯的外公是阿拉卡塔卡镇的老住户,对该镇的一切变迁,包括“香蕉”的黄金时代,他都是最好的见证人。马尔克斯曾动情地追忆过他的外公: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不得已杀了一个人。他当时住在一个镇子里,有一个恶棍老是向他寻衅。他一直没有搭理他。后来实在忍受不了欺负,就给了他一枪。全镇的人都觉得他干得好,甚至死者的一个兄弟当天晚上还横卧在他家门口,脸朝着他的房间,以防人前来报仇。马尔克斯的外公可受不了这种威胁,于是举家远走高飞,自行创建了一个城镇。
这个事件被马尔克斯在后来写进了《百年孤独》中,书中那个马孔多镇的创建人布恩蒂亚就曾杀死过一个人,冤鬼常常出现,没完没了地纠缠着他,布恩蒂亚忍无可忍便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翻山越岭,建立了马孔多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公和他是家里“唯二”的男人。外公总是亲切地唤他“小拿破仑”,小孩则回以“老爸”。当时外公已年逾花甲。他中等身材,蓄着胡子,为人沉稳,穿着整齐;在生人面前不苟言笑,在熟人面前却谈笑风生。马尔克斯几乎不折不扣地继承了外公的这些性格特征。
有一天,外孙看到了一条冻鱼,就去问外公:“那鱼为什么那么硬啊?”“因为是冻鱼。”外公回说。“什么是冻鱼啊?”“冻鱼就是加了冰的鱼。”“什么是冰啊?”于是,外公只好领着外孙去一个冰库,让他伸进手去摸了一下里面的冰块。《百年孤独》即起始于这一细节。
就是这样,马尔克斯的外祖母和外祖父滔滔不绝讲叙的许多动人的故事成了他小说世界的整整一个家族的楷模典范。
三位女亲戚
马尔克斯的三位女亲戚,即外公的表妹——表姑奶玛玛、外公的私生女——姨妈帕和外公的姐姐——姑奶娜娜,她们在外公家生活,分担了外婆的责任,同时也分享了小马尔克斯赋予这个家庭的一切烦恼和欢乐。
在马尔克斯出生之前,姨妈帕是这个家庭最年轻的成员。她聪明伶俐无所不能:洗衣,做饭,刺绣,烧糖豆,打扫卫生,叠纸玩意儿以及后来的照看孩子。《百年孤独》中的那个神奇的阿玛兰塔,据说就是以她和表姑奶玛玛为原型的。
表姑奶玛玛是个老处女,把全部的爱交给了这个家庭。因为是外公的表妹,而且是唯一跟随表哥、表嫂(尼科拉斯、特兰吉利娜夫妇)从巴兰卡斯镇迁徙到阿拉卡塔卡镇来的亲戚。她性格开朗,充满了活力,大事小事都拿得起放得下,对马尔克斯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连尼科拉斯、特兰吉利娜夫妇都得让她三分。
初到阿拉卡塔卡时她还年轻,很是引人注目,因而追求者络绎不绝。她既不拒绝,也不答应,一概以礼相待,款以自制的饴糖和果汁。和马尔克斯的外婆一样,她穿着保守,一生不是着黑就是穿灰。孩子们都很怕她,所以她承担了最艰巨的活计:给孩子们洗澡、换衣服和督促他们做作业、望弥撒。有一段时间,她还得陪小马尔克斯睡觉。
有天她正在廊子上绣花,突然有一个女孩子拿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蛋走了过来。那蛋上面有一个鼓包。那时候,外公家简直像一个解谜答疑的问询处,镇上谁有什么难事,都来问个究竟,马尔克斯至今对此依然迷惑不解。一碰到谁也解不了的难题,总是由其姨妈出来应付,而且人们总会得到满意的答复。使人最为欣赏钦佩的是她在处理这类事情时那种从容不迫的坦然风度。她转脸朝向那位拿着怪蛋的姑娘说道:“你不是问这个蛋为什么长着一个鼓包吗?”她又看了看那位姑娘,接着说:“啊,因为这是一个蜥蜴蛋。你们在院子里给我生一堆火。”等生着了火,她便泰然自若地把蛋扔进火堆烧了。她的这种从容不迫的坦然风度后来帮助马尔克斯掌握了创作《百年孤独》的诀窍。他在这部小说里,也像他姨妈当初吩咐人把蜥蜴蛋扔在院子里烧了一样,神色自然,从容地叙说耸人听闻、奇谲异特的故事,尽管,时至今日,马尔克斯仍然闹不清那究竟是什么动物下的蛋。
姑奶娜娜虽然比较孤僻,但却是马尔克斯外公的精神支柱。同样,对小马尔克斯,她与其说是真实的存在,倒不如说是一种象征:男人世界里的母系社会。那个伟大的“格兰德大妈”是她和前面这些女人共同创造的一个神话。人的性格是童年的回忆,童年是作家的“心灵故乡”和创作源泉。《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的童年是和外祖父母度过的,从出生一直到8岁之前,他一直和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外祖父母、姨妈、表姑奶和姑奶对其一生影响极大,其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常有其影子。
父母的长子
马尔克斯的父亲埃利西奥(1901—1984),1901年出生于哥伦比亚苏克雷地区的辛塞镇,他属于土生白人,也即他们的祖辈都是西班牙移民。埃利西奥是私生子,14岁才和亲生父亲相认。为了摆脱贫困和私生子的屈辱地位,他离开故乡辛塞镇,到哥伦比亚加勒比沿海城市卡塔赫纳市求学。不久即因缺乏经济来源而不得不辍学谋生。他先后流落科尔多瓦、苏克雷和玻利瓦尔等地,最后闯荡至阿拉卡塔卡镇。
从1904年到1910年,哥伦比亚马格达雷纳河流域大规模种植香蕉,使哥伦比亚的大西洋沿岸一带突然繁荣起来,形成了“香蕉热”,来自各地的人都云集在这个盛产香蕉的村镇。马尔克斯的父亲——埃利希奥就在该镇找到了一份电报报务员工作。尽管在学业上没有什么机会了,但他却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赢得了温馨的爱情。
192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埃利希奥结识了全镇最漂亮的姑娘——伊瓜兰,并爱上了她,姑娘对他也是情有所钟。他们的私恋遭到了女方父母的坚决反对。但是,姑娘对自己的情人坚贞不渝,并未婚先孕,姑娘的父母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并要求他们要远离阿拉卡塔卡镇。于是,1927年,两人移居里奥阿恰市。伊瓜兰即将分娩时,她的父母听到这一消息后,转怒为喜,老夫妇俩盼孙心切,便命女儿回到阿拉卡塔卡镇,以便使第一个外孙安全出世。1927年的3月6日,这个在日后的世界文坛上响当当的才子出世了,当时取名叫加夫列尔·何塞。
多鬼的房子
马尔克斯在8岁前跟着外祖父母居住在一座阴森恐怖的大房子(大屋)里。这座宅院的每个角落都死过人,都有难以忘怀的往事。每天下午六点钟之后,人就不能在宅院里随意走动了。那是一个恐怖而又神奇的世界,常常可以听到莫名其妙的喃喃私语声。
外公家由前院、房子和后院三大部分组成。房子颇具加勒比风格:宽敞、明亮、绿荫翳蔽的房间很多(据说有二十多间),它是《百年孤独》中布恩蒂亚家的主要蓝本。
据马尔克斯回忆,大屋的很多房间是空着的,其所以空着的原因是它们的居住者死了——可能是哪个亲戚,比如他的舅姥爷拉萨罗、姨奶佩特拉,或者姨妈玛尔加丽塔。为了纪念他们,房间一直空着。
住在那么一座大屋里,马尔克斯难免感到自己既渺小又胆怯,尤其是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房子变得静悄悄的……一到下午六点钟,大人就让小马尔克斯坐在一个摇篮里,对他说:“你别乱走动,你要是乱动,佩特拉姨妈和拉萨罗舅舅不定是谁就要从他们各自的房间里走到这儿来了。”所以,那时他总是乖乖地坐着……
马尔克斯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枯枝败叶》就描述了一个7岁的小男孩,他自始至终就一直坐在一张小椅子上。至今,人们依然觉得,那个小男孩就是小马尔克斯,在一座弥漫着恐怖气氛的宅院里,呆呆地坐在一张小椅子上。其生活环境造就了他童年时期静静地观察眼前一切的习惯。
多年以后,当马尔克斯不得不离开阿拉卡塔卡时,大屋就成了他最大的精神负担,因为他想用文学“成就它”,一半为了忘却,一半为了纪念。
迷信的外婆
外婆特兰吉利娜对于加西亚尔克斯,既是现实的,又是“艺术”的。他对她的记忆简直童话般地富有诗意。
当他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外婆就用上等的玫瑰花瓣给他治疗喉炎(据说是脐带绕脖所致)。后来,每当他打嗝或咳嗽,她就会用同样的方法给外孙治病。
母亲始终跟着父亲东跑西颠给他生下6个弟弟、4个妹妹,照料孩子的事就全交给了外婆。孩子的到来不但给大屋带来了生气,而且大大地缓和家庭气氛。孩子从未享受骑在父亲肩上逛街、趴在母亲膝下承欢的乐趣,但却很快成了外婆的宠儿。
儿时的马尔克斯总是醒得很早。每天雄鸡啼鸣、晨光熹微,外婆和姨妈起来烧早饭的时候,他也会果断地结束漫长的睡梦,回到外婆的身边。所有这些,都将进入他的记忆,成为拂不去撵不走的“幽灵”,从而最终进驻他的文学世界。比如,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第三次无可奈何》中,那个7岁的小孩在“死亡”中继续生长的噩梦,当与此不无关系。还有《枯枝败叶》中的那个11岁的男孩,他坐在摇椅上注视死人的目光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婆还是个相当健康活跃的女人,那时,她有五十多岁,她皮肤白皙、眼睛湛蓝,风韵犹存,她身材小巧,但性格坚毅。虽然头发已经灰白,但两耳皆聪,目光如炬。她始终穿着或黑或蓝的“丧服”或“半丧服”,一天到晚忙里忙外,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她总是边说边忙,自言自语,像《百年孤独》里的乌苏拉。
外婆是一位博通今古的人,她善于讲神话传说及鬼怪故事,对于马尔克斯的日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每天马尔克斯就坐在外祖母身边,听她漫不经心地一边干活一边讲的各种民间传说、寓言故事以及阿拉卡塔卡镇人民为描绘那个辉煌的“香蕉热”时代而编织的传闻。马尔克斯认真地听着,他被每一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所吸引。对于马尔克斯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外祖母往往都用一个长长的鬼故事来加以回答。和许多哥伦比亚人一样,外婆就是这样将历史、现实和迷信糅合在一起的。
因为好客,家里常常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他们有的是外公的战友,有的是其亲戚。除了朋友常来拜访外公外,外公还有很多私生子也常常到这里歇脚打尖——他和妻子是近亲结婚,担心无后,在硝烟弥漫的内战时期制造了至少9个私生子。不过,外婆却对这些私生子们没有反感,而且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地对待他们。
外祖母不仅慈祥地照顾着外孙,而且,她还是全家至高无上的女王,精明能干、精力充沛、子女成群、才识过人,她能身处逆境而不气馁,她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人口众多的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她既是家的统率者,又是带头人。因此,外祖母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频频出现,成为众多妇女角色的典型。
外公是上校
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尼古拉斯曾在“千日战争”(1899至1901年,哥伦比亚发生自由党反对保守党的内战,最后保守党获胜)中,在自由派将领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的指挥下,屡立战功,荣获上校军衔。
马尔克斯的外公是阿拉卡塔卡镇的老住户,对该镇的一切变迁,包括“香蕉”的黄金时代,他都是最好的见证人。马尔克斯曾动情地追忆过他的外公: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不得已杀了一个人。他当时住在一个镇子里,有一个恶棍老是向他寻衅。他一直没有搭理他。后来实在忍受不了欺负,就给了他一枪。全镇的人都觉得他干得好,甚至死者的一个兄弟当天晚上还横卧在他家门口,脸朝着他的房间,以防人前来报仇。马尔克斯的外公可受不了这种威胁,于是举家远走高飞,自行创建了一个城镇。
这个事件被马尔克斯在后来写进了《百年孤独》中,书中那个马孔多镇的创建人布恩蒂亚就曾杀死过一个人,冤鬼常常出现,没完没了地纠缠着他,布恩蒂亚忍无可忍便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翻山越岭,建立了马孔多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公和他是家里“唯二”的男人。外公总是亲切地唤他“小拿破仑”,小孩则回以“老爸”。当时外公已年逾花甲。他中等身材,蓄着胡子,为人沉稳,穿着整齐;在生人面前不苟言笑,在熟人面前却谈笑风生。马尔克斯几乎不折不扣地继承了外公的这些性格特征。
有一天,外孙看到了一条冻鱼,就去问外公:“那鱼为什么那么硬啊?”“因为是冻鱼。”外公回说。“什么是冻鱼啊?”“冻鱼就是加了冰的鱼。”“什么是冰啊?”于是,外公只好领着外孙去一个冰库,让他伸进手去摸了一下里面的冰块。《百年孤独》即起始于这一细节。
就是这样,马尔克斯的外祖母和外祖父滔滔不绝讲叙的许多动人的故事成了他小说世界的整整一个家族的楷模典范。
三位女亲戚
马尔克斯的三位女亲戚,即外公的表妹——表姑奶玛玛、外公的私生女——姨妈帕和外公的姐姐——姑奶娜娜,她们在外公家生活,分担了外婆的责任,同时也分享了小马尔克斯赋予这个家庭的一切烦恼和欢乐。
在马尔克斯出生之前,姨妈帕是这个家庭最年轻的成员。她聪明伶俐无所不能:洗衣,做饭,刺绣,烧糖豆,打扫卫生,叠纸玩意儿以及后来的照看孩子。《百年孤独》中的那个神奇的阿玛兰塔,据说就是以她和表姑奶玛玛为原型的。
表姑奶玛玛是个老处女,把全部的爱交给了这个家庭。因为是外公的表妹,而且是唯一跟随表哥、表嫂(尼科拉斯、特兰吉利娜夫妇)从巴兰卡斯镇迁徙到阿拉卡塔卡镇来的亲戚。她性格开朗,充满了活力,大事小事都拿得起放得下,对马尔克斯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连尼科拉斯、特兰吉利娜夫妇都得让她三分。
初到阿拉卡塔卡时她还年轻,很是引人注目,因而追求者络绎不绝。她既不拒绝,也不答应,一概以礼相待,款以自制的饴糖和果汁。和马尔克斯的外婆一样,她穿着保守,一生不是着黑就是穿灰。孩子们都很怕她,所以她承担了最艰巨的活计:给孩子们洗澡、换衣服和督促他们做作业、望弥撒。有一段时间,她还得陪小马尔克斯睡觉。
有天她正在廊子上绣花,突然有一个女孩子拿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蛋走了过来。那蛋上面有一个鼓包。那时候,外公家简直像一个解谜答疑的问询处,镇上谁有什么难事,都来问个究竟,马尔克斯至今对此依然迷惑不解。一碰到谁也解不了的难题,总是由其姨妈出来应付,而且人们总会得到满意的答复。使人最为欣赏钦佩的是她在处理这类事情时那种从容不迫的坦然风度。她转脸朝向那位拿着怪蛋的姑娘说道:“你不是问这个蛋为什么长着一个鼓包吗?”她又看了看那位姑娘,接着说:“啊,因为这是一个蜥蜴蛋。你们在院子里给我生一堆火。”等生着了火,她便泰然自若地把蛋扔进火堆烧了。她的这种从容不迫的坦然风度后来帮助马尔克斯掌握了创作《百年孤独》的诀窍。他在这部小说里,也像他姨妈当初吩咐人把蜥蜴蛋扔在院子里烧了一样,神色自然,从容地叙说耸人听闻、奇谲异特的故事,尽管,时至今日,马尔克斯仍然闹不清那究竟是什么动物下的蛋。
姑奶娜娜虽然比较孤僻,但却是马尔克斯外公的精神支柱。同样,对小马尔克斯,她与其说是真实的存在,倒不如说是一种象征:男人世界里的母系社会。那个伟大的“格兰德大妈”是她和前面这些女人共同创造的一个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