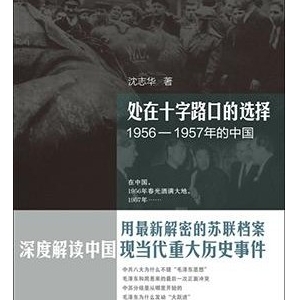《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教授
简介
1956-1957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不寻常的年度,这是反差极大的两年: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为什么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却做出了如此选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著名学者沈志华教授爬梳国内外文献史料,描述这一历史过程。
精彩书摘
·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还是“自己人”?
195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尽管冰雪尚未融化,中国大地已经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说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动态。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像一支报春花,预示了中共领导人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充满理想和信心的蓝图,也标志着中共将对其执政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知识分子会议前夕,毛泽东正在筹划一个新的宏伟蓝图,即在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三大改造将要提前结束的形势下,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尽快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从合作化到工商业改造,汹涌而来的全国社会主义热潮,强化了毛泽东改造中国的自信。同时,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党内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发热。国务院各部委召开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然而,与广大农民、工人和干部摩拳擦掌的热情相比,作为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之一,知识分子则多少显得有些不够振奋。
这些留下或归来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政治信仰多么复杂、多么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爱国。虽然不一定认同共产主义,甚至对此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因此,多数人倾向于中共新政权,希望有机会为国家效力。
不过,在共产党看来,这批知识分子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要让他们为新社会服务,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对于建国之初中共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界究竟是被迫承受还是主动反省?有一种估计是比较客观的:大概在运动之初,主动反省成分多于被动承受。正是由于愧疚感和感恩情结,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承认有自我改造的需要,自愿地接受了中共起初比较温和的思想改造要求。
然而,接下来的运动却日趋激烈。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一步步形成了政治围攻,知识界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些运动未必能打碎知识分子埋在心底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但可以迫使大多数人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立场和观念。显然,毛泽东要使资产阶级思想“名声扫地”,事实上也就要先使知识分子“名声扫地”。最严重的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1955年由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的肃反运动。根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苏联通报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划定的范围内,工人、职员、现役军人、科学工作者、大学生,一直到乡一级的所有干部,都属于肃反审查之列,拟定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到9月中旬时,已经“仔细审查了”222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分子、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派别。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不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这种现象在文艺界特别突出。
显然,这种状况对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极为不利。于是,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便提上了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动议,来自于周恩来和李维汉,这不是偶然的。周恩来的出身、修养和秉赋,以及在上海和重庆工作时期同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密切交往,使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理解和沟通,并与许多高层文化名人私交甚笃。建国初期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从海外回来,主要就是他的努力结果。
但是,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并非没有阻力。中共领导人早就意识到缺乏知识分子对于经济建设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中下层干部,就是在最高层领导人眼里,也大都把知识分子看作“异类”。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对于中共和知识分子两方面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按照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的说法,“就有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危险。其实,这里不只是可能性,而是必然的结果。试想,知识分子掌握着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知识和技术,而这种资源(或曰知识产权)却不像资本家和地主的生产资料那样可以剥夺。那么,从理念上讲,共产党人要实现社会公有化,就必然把“异己”的知识分子本身作为革命对象。执政党不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甚至还要作为革命对象,其结果无异于在“自毁长城”。周恩来并非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他的报告也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总体状况时,报告认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但在具体分析知识分子状况时,报告仍然指出,其中落后分子占百分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更何况还有与先进分子数量相等的中间分子。这与“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总体判断明显地是相互矛盾的。很可能,周恩来这样讲是考虑到了党内多数人的估计。陆定一在发言中说得十分明白:“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了使我国变成为先进的国家,而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
知识分子本来是具有爱国主义情感和立场的社会主体的一部分,却偏偏要把他们看成是依附于某个阶级的“毛”,非经过一番“脱胎换骨”乃至“急风暴雨”的思想改造就不能为国家社稷贡献自己的知识,这种从本质上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理念就决定了中共这次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不可能是彻底的。正因为如此,当1957年知识分子受到党的鼓励和动员,又一次表现出独立思考的本性时,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钟摆立即就回到了1955年,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10年后“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横扫一切“臭老九”的种种举动,则是把中共对知识分子怀疑和敌视的“左”倾错误发挥到了顶点。
毛泽东与童第周、华罗庚等知识分子在一起